文心不老 碧樹長青
——“小兵張嘎之父”徐光耀訪談
11月16日晚,廈門,第3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上,當主持人宣布河北作家徐光耀獲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電影)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一時掌聲雷動,臺上臺下,太多人淚盈于眶。“小兵張嘎之父”徐光耀,這位99歲高齡的老人,經歷了中國近一個世紀的變遷,走過戰火硝煙,又見證了國家的繁榮發展,把自己的家國情懷和對家鄉冀中大地的熱愛寫進一部部膾炙人口的作品中。如今他迎來了屬于自己的終身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次日下午,本報記者帶著家鄉讀者的祝福拜望了徐老。

11月17日,徐光耀在接受河北日報記者采訪。河北日報記者 史晟全 攝
“快來快來,好久不見了。”一進房間門,就看見徐老笑容滿面地坐在沙發上沖我們招著手,對襟盤扣的紅色中式上衣,襯得老爺子格外神采奕奕。
徐老從剛剛替他領獎歸來的兒子徐丹手里接過獎杯,使勁地舉起來,輕搖了兩下,開心得像個孩子。“太沉了,我都快要拿不動了。”在場的人都笑起來,都明白他說的這個“沉”可不只是這個獎杯的實際重量,更是人民給徐老的沉甸甸的肯定和信任。

11月17日,手捧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電影)獎杯,徐光耀十分開心。河北日報記者 史晟全 攝
分明地,老人眼中的笑意里有一層淚花浮上來。“我特別感動。因為他們評價我是個身經百戰的人民戰士,是從硝煙里頭走過來的文學作家,我覺得給我終身成就獎,不光是看到了我在電影上的一些工作成績,更多的是看到了我的歷史。我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我覺得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人民沒忘記我,給我這么高的一個獎項,讓我很感動。”
隔著這層薄薄的淚光,徐老的眼睛越發炯炯有神。在他的娓娓道來中,我們似看到冀中平原上一個稚嫩的小戰士,櫛風沐雨,從時光隧道中奔跑而來。
從土八路到“半作家”
徐光耀出生在河北雄縣段崗村,13歲就參加了八路軍,剛穿上軍裝時,“大得能裝下我這樣兩個人”。因為只上到小學四年級,文化水平實在有限,家信都不會寫,想跟家里說點什么只能請文書代筆。但是文書寫出來的家信開頭就是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接著就是“兒參軍以來,身體健康,平安無事。”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寫法讓這個初次離家的少年憋屈得不行,“話在肚子里啥都倒不出來,想告訴家里自己來了部隊壯了、胖了也說不明白”,一著急,干脆自己照貓畫虎學著寫,慢慢地不用求人了,徐光耀挺高興。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徐老有寫日記的習慣,卻不知道這個習慣能一直倒追到80多年前。“我最早寫日記應該是在1941年。過年的時候,老百姓慰問八路軍,送來一些小本子,我就要了一本。那會兒紙都很難找,那么漂亮的小本子,我非常珍惜,想著在上面寫點什么呢,記日記吧。”
徐光耀一開始是背著別人寫日記的,因為怕人家笑話。后來索性公開了,記得都是些日常非常瑣碎的事。有一次,旅長王長江到徐光耀工作的鋤奸科,看見他的日記本在桌子上,翻開看了看說:“小徐,你怎么把花了一毛錢買花生也記到日記上啊?”徐光耀說:“一個月發我一塊錢,我花十分之一買花生,這就是個大事。”后來經常行軍打仗,背不動那么多東西,徐光耀把日記本藏在房東家里,結果再沒機會回去找,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可惜。
除了日記,徐光耀還寫連隊的工作總結、寫宿營報告之類的。越寫越熟練,慢慢地試著寫一些戰地通訊等給報紙投稿,居然很多都能發表了。有一篇文章叫《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組》,在《冀中導報》分兩期刊登,有三四千字,反響不小。
也正是因為常常在報紙上寫文章,徐光耀的名字在軍分區有了點小名氣,這也為他能到聯大學習提供了底氣。所以當1947年初,他拿著一本貼滿自己在報紙上發表的作品的剪貼簿,找到聯大文學系想看看有沒有學習機會的時候,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復。
1947年初,徐光耀成了聯大文學系的插班生,這對他來說有著很大的意義。作為一個全靠自己琢磨的土作家,到聯大后,終于有機會從文學的基礎要素、文學的基本理論學起,這些基礎知識,給他日后的寫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徐光耀尤其喜歡蕭殷講的“創作方法論”,上他的課聽得特別仔細,“他還經常會在我的筆記本上指點幾句,這對我日后寫作幫助很大”。1947年2月27日,解放區《冀中導報》副刊發表了徐光耀以筆名“越風”寫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周玉章》。這篇文章是他被分配到連隊深入生活,正巧連隊打了一仗之后,戰士周玉章發生了一個小故事,徐光耀就打算給連隊的墻報寫篇小文章,寫完之后覺得太長了,在墻報上發表不合適,就帶回聯大整理后寄給了《冀中導報》。沒想到發表后反響特別好,他從此正式走上創作之路。
經過8個月的學習,徐光耀在寫作上有了質的變化。從土八路變成了一個“半作家”。也正是這個修煉,為徐光耀在兩年后創作長篇小說《平原烈火》打下了文學素養功底。
抗戰情結影響一生
親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先后經歷了上百場戰斗,這一切讓徐光耀成長為一名堅強的人民戰士。直到現在,一次次的浴血奮戰,一次次戰場上的堅守與犧牲,一張張并肩戰斗的戰友的臉龐,還會時常浮現在徐光耀的眼前。也正是這血與火的親身經歷,讓戰爭題材成為徐光耀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
“我大部分文章,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劇本都是寫戰爭題材。我一生最大的情結就是抗日戰爭。”8年抗戰,給徐光耀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敵人太兇殘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面對敵人的瘋狂掃蕩,冀中軍區部隊奮起抵抗。他們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無數將士為國捐軀。
在戰爭最殘酷的那幾年,徐光耀在縣大隊工作,那是最基層的八路軍武裝,所以《平原烈火》一開頭就寫環境的殘酷、鬼子掃蕩的兇狠毒辣,而那些都是他親身經歷的。我方與敵人的火力相差懸殊,只能靠兩條腿跟敵人的汽車、坦克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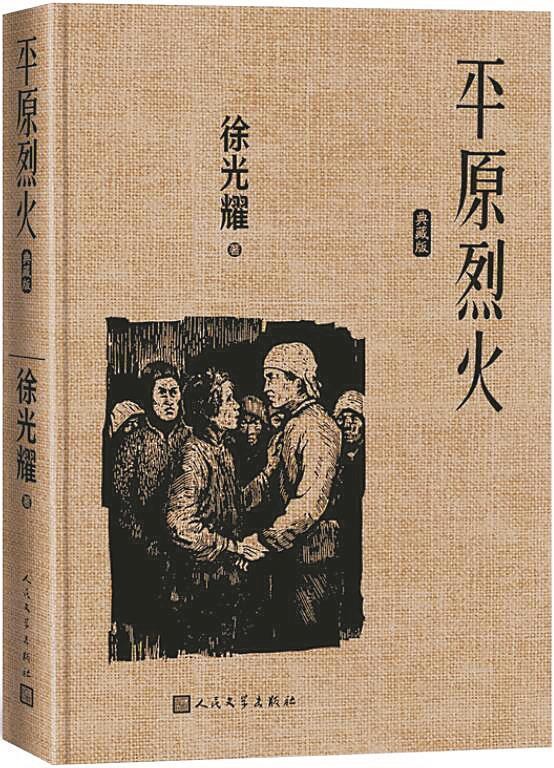
《平原烈火)封面。
《平原烈火》主人公周鐵漢的原型叫侯松坡。徐光耀清楚地記得,侯松坡被敵人逮住,越獄出來,他兩個膀子被敵人打殘了,回到部隊后行軍的時候不能背槍,他夾著槍跟著部隊打仗,最后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
創作的日子,徐光耀至今想來歷歷在目。那時,他把自己關在屋子里,將先烈王先臣司令員的遺像掛在墻上,使之正對書桌,一抬頭便見司令員的微笑。創作的過程,徐光耀好像重回戰場,跟眾多戰友們一起,重新再經歷一次,他流著淚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年齡就離開的戰友們的故事,心里滿是痛惜。
1950年,小說在《人民文學》甫一發表,立即引起廣泛關注。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早期描寫共產黨艱苦抗戰的長篇小說,為之后革命戰爭題材創作鋪下堅實基石。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就是這部《平原烈火》。
“我的很多戰友、同志都犧牲了,提起他們,我很難過。是先烈們用生命架橋鋪路,讓我活了下來,我分享了他們的榮光。”說到這些,徐老的聲音里有了幾分哽咽。
最愛白洋淀上嘎子哥
在徐老床側對面墻上貼著一張版畫《烽火歲月——小兵張嘎和玉英在白洋淀上》,葦叢中,兩個少年坐在船頭,笑得一臉燦爛。

電影《小兵張嘎》劇照。
“白洋淀風光好,英雄多,到處都有嘎子哥。”徐老只要說起嘎子,就如同說起自己的孩子,滔滔不絕,喜愛之情藏都藏不住。從嘎子形象塑造出來到現在,轉眼已經60多年,“小兵張嘎之父”已是世紀老人,嘎子卻還是幾代人心目中那個嘎氣十足的少年。在新鮮IP層出不窮的當下,這個嘎小子為何能依然保持著歷久彌新的魅力呢?徐老說,老師丁玲曾經囑咐過自己“要狠狠地寫人物”。要想在文學作品上寫出人物的典型來,這個人物一定是一類人或者一群人的代表,這個形象一定是活的,并且一定有著很多很多的故事。
誰能想到,嘎子這個鮮活有趣的形象卻誕生在徐光耀人生最低谷的時候。1957年,徐光耀回家閉門思過。“我在家待著就看書,想把憤懣的情緒壓下去。我看了很多書,想總結一下有什么收獲,但腦子卻一片空白。有一天我正在門后站著胡思亂想,一歲的女兒從對面的屋子蹣跚著走來,想讓我跟她玩兒。我那時候就想:我自己的事情還弄不清呢,你又來給我添麻煩。我就朝她大吼一聲,把孩子嚇跑了。”
徐光耀也被自己的舉動嚇到了,反復思考后,決定靠寫作“集中精力、轉移方向”。寫什么好呢?想來想去,他突然想起《平原烈火》里有個小鬼“瞪眼虎”,出場時挺活躍,可后來被主角擠到一邊去了,沒啥事可干,最后只能蔫兒不唧地結束,一位老戰友還跟他抱怨過:挺可愛一個孩子,怎么給寫丟了呢?徐光耀瞬時靈光一閃,現在就把他抓回來吧,能逗自己笑的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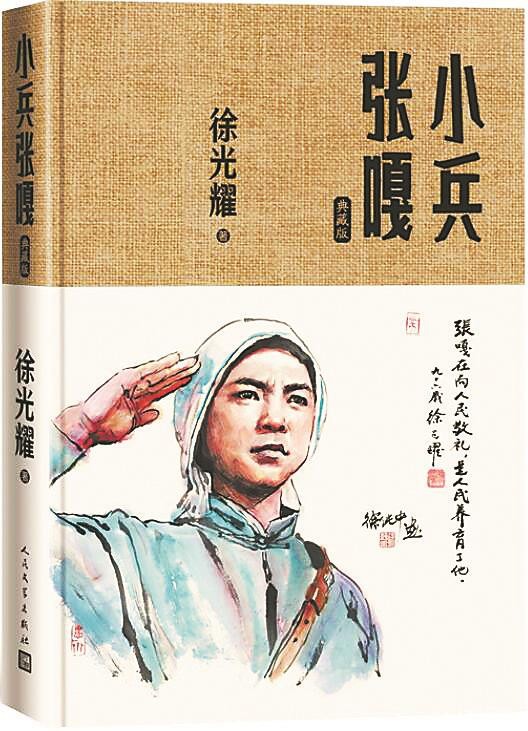
小說《小兵張嘎》封面。
徐光耀總愛說自己的性格是刻板的、機械的,所以格外喜歡調皮搗蛋的孩子。參軍以后,他發現平時調皮搗蛋、嘎里嘎氣這些人,在戰場上也是英勇無畏的。尤其是每當遇見了艱難、危險的情況,他們總能想出辦法來解決,這一點讓他羨慕不已。
決定找回“瞪眼虎”后,徐光耀把平生所見所聞、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開始在腦子里廣撒大網,盡力搜尋,桌上放張紙,想起一點記一點,想起一條記一條,很快地,那些大嘎子、小嘎子、老嘎子、男嘎子、女嘎子,全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
至于嘎子的原型是誰,徐老說太多的人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他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這些大嘎子小嘎子的嘎人嘎事讓這個人物活起來了。盡管如此,說話間,他突然想起一個讓自己印象深刻的嘎孩子。“大概是1944年,我在寧晉縣大隊當特派員,鄰縣趙縣縣大隊有兩個特別調皮的小偵察員,都在十四五歲之間。其中一個外號就叫‘瞪眼虎’,他倒挎馬槍,斜翹帽檐,渾身嘎氣,我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忘記。”徐老開心地比劃著,一個經典形象讓他記了幾十年,這個“瞪眼虎”可以算是小兵張嘎的萌芽吧。
愛生活也愛這片熱土
回想創作歷程,徐老說起自己非常喜歡的兩個字——鑿真。他覺得做事情要嚴肅認真,就是從石頭里面刨、鑿,鑿真理。而自己這一生就是占了這個便宜。喜歡文學的他,常常在文學上“鑿真”,讀一些文藝作品讀得很著迷。正因為著迷,就能夠比較快、比較多地吸收一些東西。
對于文學創作,徐老確實秉持著一股較真的勁,“我不敢說自己寫了很多優秀的作品,但是我在創作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創作電影、小說、戲劇等,都要力爭出精品。寫一般的東西,人們也會看的,但是看過就忘了。只有寫出精品來,寫出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東西,才能讓人記住”。
在徐光耀看來,要想出精品,從主觀上,自己要非常非常努力,不是拿出一般的勁頭來,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在客觀上,必須要投入到生活中去,有了生活基礎你才能夠真正寫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來。
從《平原烈火》到《小兵張嘎》,從《四百生靈》《望日蓮》到《昨夜西風凋碧樹》《向死而生》,無論何種題材,無論何時何地,徐光耀的作品里沒有任何炫技的文字和寫法,甚至因為質樸而帶有那么一些土氣,但是就讓人讀來勁道生動,三言兩語間,畫面人物就能活靈活現地站在讀者面前。房東女兒的眼睛、各地戰友的方言土語、老妹子一生氣就上房的舉動……單是《昨夜西風凋碧樹》里讓人難忘的例子就不勝枚舉。
“感覺您不是在刻意描寫場景,而是您就在火熱的生活中體驗著、沉浸著、記錄著。”對記者這個說法,徐老連連點頭。他想起1952年丁玲在給他的回信中說:“我勸你忘記你是一個作家……你專心去生活吧。當你在冀中的時候,你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寫小說,但當你寫小說的時候,你的人物全出來了。那就是因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對生活是老實的,你與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邊,在斗爭里邊,你不是觀察生活,你不是旁觀者……”在徐老看來,寫作的時候應該老老實實地忠于生活,應該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寫。“我有自己的好幾個語匯本子,跟老百姓、跟戰士、跟朋友談話的時候,有一些很精彩的語言,比如成語、歇后語、方言,我就把它記下來,記了好幾個本子。”
徐老依然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他讓徐丹拿出了自己最新的一本日記給我們看。字跡清秀工整、筆劃清晰有力,很難相信這是一位百歲老人寫下的。徐老說,年紀大了,住在醫院里,日子回歸平淡,精力也不似從前,所以變成了寫周記、月記。“你看這寫的是,前幾天有老友來探望我,很是開心。”而這一次,徐老也會把獲獎這件事認認真真寫下一筆。
徐光耀深愛著生活,也深愛著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白洋淀,青紗帳,鉆天楊。冀中平原是徐光耀生長和戰斗過的地方,他深愛這方熱土。徐光耀說忘了什么也忘記不了冀中,也不敢忘記,提起冀中就有種深深的驕傲感和自豪感。
“我能獲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對我是一種很大的榮光,也是一種很大的幸福。《小兵張嘎》的背景冀中跟我非常密切,是真正的一種家鄉的感情。因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給了我們八路軍解放軍很大的支持、很大的愛護。我永遠感激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為這片土地的人民寫一點反映他們生活和戰斗的故事,我自己也感覺到是一種榮幸。”徐老在獲獎感言中如是說。
徐老說自己就是雄安人,看到日新月異發展中的雄安新區,感到十分激動,現在故鄉的人民很幸福,他們有著更光明的前途。
每次提起嘎子,徐老都會說,我特別喜歡他的性格,羨慕他的性格,但是我自己的性格刻板、機械,我不滿意。可是,他在文學作品、電影臺詞和日記里,不經意流露出來的幽默、有趣,甚至是幾分孩子氣的促狹,總會讓人隱約間看到嘎子的影子。捧著沉甸甸的獎杯,聽大家說著“實至名歸”,徐老一個勁地擺手,“不敢當不敢當”,他說自己只是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秉持著一腔熱血,努力前行著。(河北日報記者 韓莉)


 數字化轉型促發展
數字化轉型促發展 非遺面塑進校園
非遺面塑進校園 初冬美景入畫來
初冬美景入畫來 打造冰雪裝備...
打造冰雪裝備... 濕地雁影舞翩躚
濕地雁影舞翩躚 河北遵化:中...
河北遵化:中... 雄安1000千伏...
雄安1000千伏... 候鳥翔集衡水湖
候鳥翔集衡水湖 雄商高鐵河北...
雄商高鐵河北... 長城訪談丨唐...
長城訪談丨唐... 天下無詐 | 取...
天下無詐 | 取... 河北藁城:公...
河北藁城:公... 微紀錄片丨問...
微紀錄片丨問... 長城專訪|高...
長城專訪|高... 記者節MV | 我...
記者節MV | 我... MG動畫|霜風...
MG動畫|霜風... 主播說雄安丨...
主播說雄安丨... 大河之北丨尋...
大河之北丨尋...